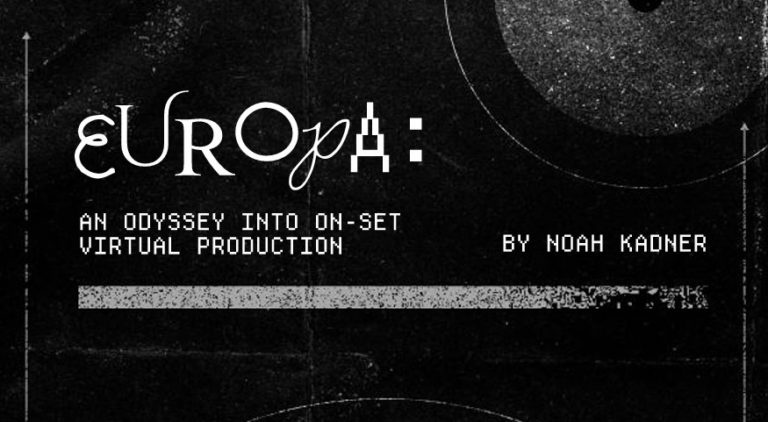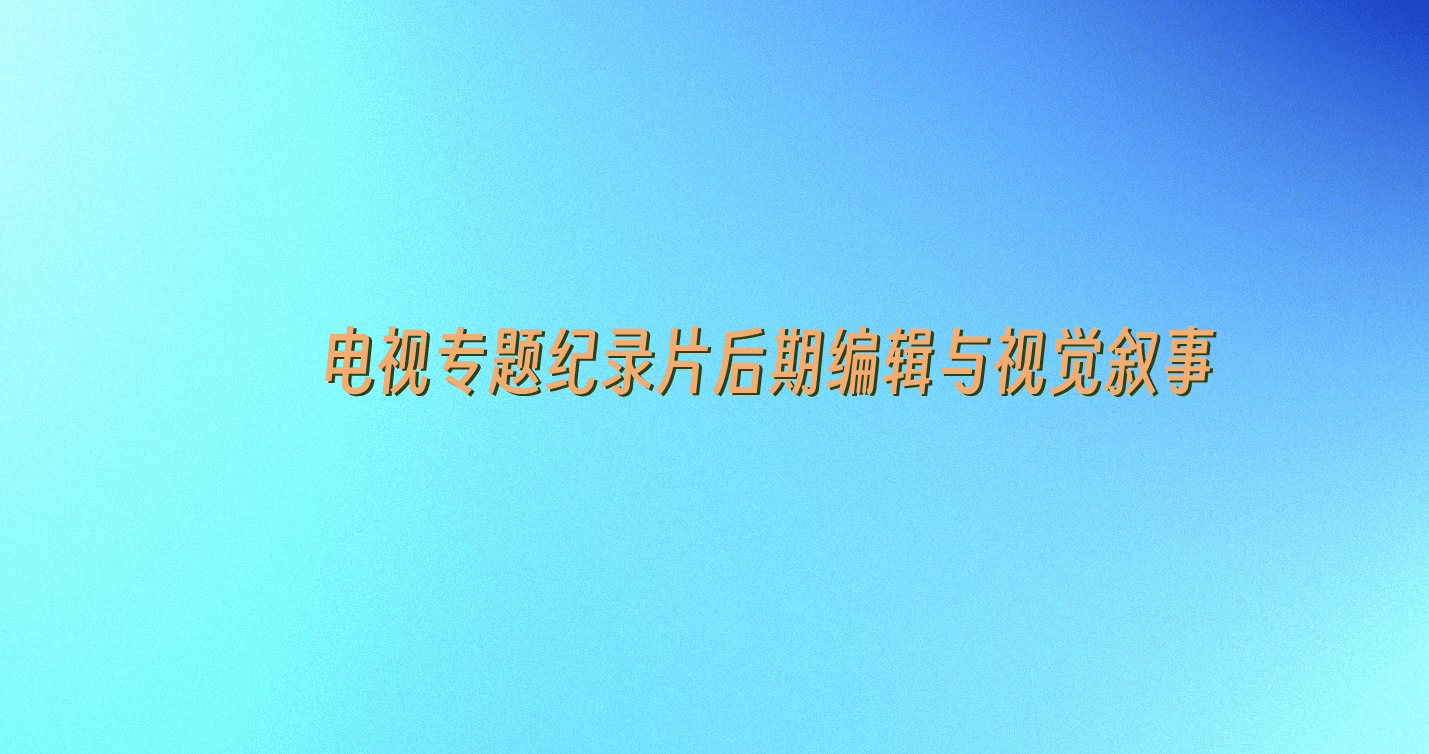一、语境:意义生成的理论
日本新生代导演的艺术电影创作之法,受益于时代性外部环境的变革和电影体制自身的变革。众所周知,日本电影一直在好莱坞传统和自身民族传统之间游刃有余(或者说伸缩自如)。对日本民族主体性的追寻,也一直是其成为日本导演的自觉。新生代导演团体(诸如富田克也、深田晃司(Koji Fukada)、三宅唱、滨口龙介、真利子哲也、小森はるか)中,这种意识更是强烈。
日本电影艺术表现的传统,除了在美国和民族之间的周转,法国等电影艺术的涵养也自然不可小觑。北海道大学的电影学博士黄也就介绍:“电影美学校”(映画美学校,THE FILM SCHOOL OF TOKYO)成立于 1997 年,它是一所在法国电影文化中心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民办的电影教育机构。立教一派成员作为该学校最初的教学主体,他们各自分享自身的创作理念与经验,培育了大量的新生代电影导演。(黄也)
无独有偶,黄也博士的导师——旅居北海道大学的应雄教授的《德勒兹<电影1:运动 — 影像>中的“运动影像》(题名的拗口之处,恰恰是凸显了此文所阐释意义的晦涩之本质所对应的措辞和言语策略)中的“价值”,是在分析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关于运动和电影运动的著名命题之一(即运动应该从运动所通过、所覆盖的空间中区分出来,它是通过、覆盖的行为)的阐释中凸显出来的。法国成为日本新生代电影创作,或者学者建构电影理论的一种“资源”而存在。
我们回到《德勒兹<电影1:运动 — 影像>中的“运动影像》一文,在众多的柏格森抑或是基本是对于这个命题的再阐释的德勒兹的《电影1:运动》——的电影理论解读的文本中脱颖而出,其价值恰恰在于点题:即电影的空间场面调度和镜头的配置——在原理上是背离真实的道理。柏格森(抑或德勒兹)对于电影虚假性的论断,是从下面的关于“何为运动?”和“何为电影的运动?”之差异性论述中体现出来的:
这些位置或瞬间的点,是一个完整的运动中不动的“切片”,而非运动本身。假定一个从A地点到B地点的运动,中间它经过了C、D、E的位置。所有这些A、B、C、D、E的点累加起来,不等于通过这些点的运动。(应雄:7)
换言之,电影有一种从拍摄到观众观影的媒介运动。一开始是整个摄制和导演团队对于所拍摄对象和拍摄活动本身的——三维立体的布置,这个活动中涉及的美学和伦理的丰富性,柏格森和德勒兹都有详尽的论述。然后是制作(洗印、剪辑、配色、合成),最后是通过电影院空间、银幕和声音、灯光等设备的辅助得以实现的声画效果的呈现和观众的接受活动。这个过程——笔者之所以这样啰嗦,恰恰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电影远非我们所想的简单。事实上,这整个过程的配置和选择,已经高度偏离了所谓原始真实性的——维度。这个命题,与安德烈·巴赞的命题刚好错位。在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理论中,电影的真实性、写实性维度是最为显著的代表。我们可不可以说,作为哲学家的柏格森的命题,一经出现,便似乎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作为电影理论家的巴赞命题的有效性。
或者说,两位大师,所言的地方,完全在不同的意义领域。柏格森通过电影摄影机和电影的一套工业流程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与客观世界的背离”特征出发,而巴赞在论述摄影机所摄录的这个对象世界的真实有效性(意谓电影影像即客观动作的残留)。在巴赞的论述中,并没有涉及摄影机所摄录对象的胶片的速度和镜头对准事物的角度、切片等符号学上的索引有效性问题。依笔者理解,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一书中所言的,大部分是电影的生活真实、伦理真实和现象学真实。
值得肯定的是,应雄教授通过对柏格森哲学的解读和阐释——言简意赅地传递了柏格森和德勒兹命题所言的“电影媒介的哲学真实”。如在柏格森关于“运动和瞬间”这个电影拍摄、制作和播映时最为关键的场域,应雄教授一言蔽之,用“换句话说,用空间中的位置或时间中的瞬间,是无法还原通过、覆盖这些位置的运动本身的”这样的解读,抵达了对于柏格森关于电影运动论断——的评述。
诚然,从电影运动的虚假性——它的实质是与观众产生认知的互动——出发,电影生产(包括导演的场面调度、拍摄,以及演员的表演)就成为了一种可以不断协商、挪用经验和他者文本的一种实验活动。这一点,应雄教授教授阐述得比较到位。譬如,在论及费穆的《小城之春》时,应雄教授抓住了费穆在影像实验中的“重复”和“差异”等问题(在影片开头部分周玉纹买菜回家,走进厨房的瞬间,和后来将菜交给礼言的瞬间,分别有两次独白。这两次独白和影像传递的信息之间,呈现了对等和不对等的关系,其功能,即为差异和重复)。等于将德勒兹的命题,和早期中国电影中的独白和影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哲学、艺术解读。毫无疑问,这种解读是抓住电影的本义的。再如,论及香港武侠片宗师张彻导演时,应雄抓住了与另一位武侠片大师胡金铨“禅机闪现般的风格”的对比。如果胡金铨采用极简和残缺,张彻则采用“过剩”和“笨拙”,甚至“滥用”。电影的意义,正是在日常生活世界里被唾弃的“滥用”,在银幕媒介的作用下,得到了重新焕发光彩——这种特殊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中得到充分呈现的。
而在“从运动影像到时间影像”的这另一个重要的命题中,应雄教授截取的也是凸显电影时间本质的德勒兹话语:“数字,有时作为独立的维度、有时作为它所测定的东西的附属物而出现”继而等于也通过抓住电影时间的两种本质形态,等于了论证了电影时间本身的具有的符号性和反符号性的双重维度。而这与本文开头所援引的柏格森命题之一(运动和对运动的阐释和符号化)是一脉相承的。
客观而言,应雄教授所处的文化语境,结合了西方(法国语境为主)、东亚(日本语境为主)和母国(中国的语境)三者对于意义的生成世界的理解和实践,等于也会自己开展比较富有说服力的电影研究敞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而在“好莱坞与民族性”、“法国电影新浪潮遗韵”属于电影工业内部的美学传承中,日本电影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影美学校与东京艺术大学,实际上拥有同一批电影教育者,即立教一派成员。他们作为滨口龙介、三宅唱等新生代导演的指导老师,在其创作主体的构建过程当中产生了无法忽视的作用。进而言之,从 20 世纪 80 年代立教新浪潮开始,到现今新生代导演的创作群体现象,当代日本电影当中存在着一条明晰的作者电影的师承脉络。这意味着,探寻新生代导演创作主体性问题的同时,需要追溯立教新浪潮导演创作主体的源头。这股风影响了日本新生代导演的艺术口味。即黄也博士援引黑泽清的陈述对日本电影新生代的一种集体评价:“莲实重彦讲义是一门关于观看、倾听的电影课。我们现在仍体验着‘莲实’(的方法)……。这与其说是一种意识,不如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黄也)
这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导演“作为电影导演的出发点”,它们并不在于其题材和手法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一种更为现代(或者当代化的手段),即“演员身体存在感的凸显”、“作品中去语境化、去历史化”(譬如,他们还十分在于演员的“脸”的价值等呈现)等特征,三宅唱即这种新生代导演的代表。

二、三宅唱电影中的意义生成方法简述
黄也指出:“三宅唱作品当中既不存在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中的英雄,也没有艺术电影里常见的底层边缘人物,即对社会历史事件表现得漠不关心,也从不会通过戏剧性的冲突去表现人性,而是像埃里克·侯麦的电影一样,始终聚焦于普普通通的青春男女的日常生活、情感动态。”
同样,在论及日本新生代著名导演三宅唱的“镜头特征和伦理”时,应雄教授所采用的学术之法也依然是贯穿东西文化观的语汇交流基础上的文本细读。具体而言,应雄教授是通过对三宅导演的《无用之人》(2010)、《你的鸟儿会唱歌》(2018)、《惠子,凝视》(2022)等电影的文本分析基础上界定导演的艺术风格的。在对三宅唱的长篇处女作《无用之人》(2010)的分析上,应雄教授的观察独到而精准。
他观察到——
冬天的北海道,三个高中生(哲雄、岩、谷)在一家制造保安设备的小公司打工。这一天他们骑车来公司,哲雄和谷各骑一辆自行车,岩则站立在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部。远处公司的小卡车陷在雪里,站在自行车上的岩迅速下车向卡车的方向奔跑。在一个长镜头内,他跳下自行车,跑着绕过房屋建筑,一直跑到陷在雪中的卡车边,帮着开卡车的公司员工伊丹推卡车。其间我们能听到铛铛铛铛的警笛声(……表明即将有列车通过)。追着他的移动镜头里,方才已经被甩在镜框外的另两个骑自行车的高中生也奔跑着从右方进入画框,来帮着推卡车,与此同时,镜头内后方纵深处,一辆城际列车从右边入画,横切穿越画面向左方出画。
……不久,又出现包括这三个高中生在内的数人从坐向右赶来、进入公司房屋的镜头。小卡车打着车灯从画面左深处缓缓驶来,向右边行进。车后哲雄和谷骑着自行车跟进,岩则站在卡车上。他跳下卡车,向右方小跑,打开挡住车道的栅栏。
在这个连贯的镜头组接中,有一个人被拉下了,那就是岩。应雄教授观察到——
这是一个在精心设计、拍摄下完成的以实现”浑浊“或”混乱感“”不精心“的影像效果的镜头。首先是镜头前半段内的三种移动手段,即卡车、自行车和人的徒步。本来就可以是安排一辆卡车和三辆自行车自左向右的移动,但导演偏偏让三个高中生骑两辆自行车,于是就“剩余”出一个人(岩),他起初是站立在卡车后部的,随后是徒步,时或行走,时或奔跑。正是“剩余”出来的他的移动方式及其诸般状态,极大地激活了画面。……这种偏爱里恐怕有导演的某种艺术直觉,似乎是在演示如何让镜头更鲜活、如何让世界看起来更魅惑,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有“剩余”存在,有“剩余”在悄然发力。
通过三宅唱这种迥异于好莱坞电影(或者一般剧情电影)叙事的方法,应雄教授也等于解剖出了导演“三宅唱选择的不是叙事的逻辑严密或画面的条理清晰,而是画面内运动的量的增值。”
除了对于三宅“运动的量”的发现,应雄也发现了三宅影片里“无意味”“非命名”的发现,暧昧与清晰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身体”与记录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呈现。在《你的鸟儿会唱歌》的结尾,佐知子郑重地向“我”坦白说打算跟静雄作为恋爱对象相处,对此“我”嘴上依然在说你俩该在一起。两人走出咖啡馆在街上各自分开后,“我”终于撑不下去,突然快跑追上已经走远了的佐知子,气喘吁吁地说刚才我撒谎了,我喜欢你……画面是佐知子满脸复杂的表情,影片就此结束。针对这一幕,应雄教授在分析了导演自己的说法之后,入木三分地分析道:“……诧异,怨,感谢,轻蔑,暖流,谛念,期待……都是,又都不是。……感情间不断地重合性交替,是这个脸部表情的定义,其中没有任何某种感情获得单独的主宰地位,这就是它的暧昧。同时,这也是它的清晰,即感情在本性上区别于冲动,它不导向动作,而只是保持它纯感情的潜在本性,必然作为一个‘复合体’持续绵延,这是只有在身体层面上才能实实在在地体验、再生的经验。”应雄教授,用柏格森的学术词汇“绵延”,进行对三宅电影的风格界定,这是一种符合导演真实表现手法的“呈现”,可谓接通了导演自身的方法和实践世界。两者之间,做到了天衣无缝,或者说京可能地做到了客观——而这一点,正是理论家和评论家恪尽职守的地方。同时,在对《惠子,凝视》这部电影的分析中,应雄教授抓住的依然是柏格森(德勒兹)命题:影像本身的“无意味”“非命名”特征。这些影像驱逐了符号,还原到了真实的“像”。
换言之,应雄教授抓取的是三宅唱如何迥异于好莱坞电影的表意之道——进行一种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和贯通的艺术表意实践,其镜头伦理中蕴含着深深的日本性。
 三、三宅唱工作坊带来的启示
三、三宅唱工作坊带来的启示
鉴于三宅唱导演在电影界的地位,以及其导演方法的独特性,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在应雄教授、黄也老师的牵线下,不仅受聘于电影学院,成为客座教授。更是在2025年亲自来到桐乡校区的这家学院,开张暑期工作坊。工作坊开设“72小时场景创设实践”环节。其方法也是独特的,在工作坊期间,三宅唱导演为本工作坊提供一份“原创剧本”。参与者将根据三宅唱导演撰写的剧本,以每十人左右一组进行分组,在限定的72小时内,以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为场地,共同创作并完成一部短片。三宅唱导演将在创作现场,对每组创作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在6月30日,在华影楼剧场,三宅唱导演更是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附带现场导演指导的)导演工作方法论讲座。
现场,三宅导演主要分享了(或者东西文化语境迥异)三部电影的桥段,进行现场讲解。
案例1:《不可饶恕》美国版和日本版的区别在于文化语境的区别
《不可饶恕》(1992)美国版为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一部复仇电影(或者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行使公正道义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转折桥段,即促成主人公去行使这个举动的转折点。通过镜头的布局,伊斯特伍德营造了这个观众看得很清楚的剧情转折。表现了主人公本来是为了钱而去战斗,看到了女子的面容,他改变了——为了眼前面容善良的女子而战。
而在日本改编版、李相日导演的这部《不可饶恕》(2013)中,在这个桥段的处理中,同中有异。其中,与美国版不一样的场面调度,最为显著的是,在日本版的这个桥段中,被毁容的女子一直没有回头。导演造就了一种日本民族特有的电影影像表意系统。故事中这个求助动作的主人——女子,一直没回头,也意味着,即将来临的“回头”这个动作,必然即是重要的时刻。同时,在日本版的电影中,在这个桥段中,设置了迥异于原版(或者溢出于美国好莱坞式剧情)的桥段,男主人公的一些往事被带起,成为他改变的动力。同时,音乐也极度渲染了这种东方的意蕴。在一个复仇的故事里,总式有爱恨情仇,总是有对于自己往事(过往行为)的检讨和救赎的成分。这成为东方复仇故事(帮助故事)迥异于西方复仇(帮助)故事的地方。

案例2:《你的鸟儿会唱歌》:场面调度和演员身体动作和表意之间的关系。导演和演员不断试错,不断调整——得到最恰当的场面布置
三宅导演的《你的鸟儿会唱歌》有这样一个桥段,故事两位主人公(佐知子和“我”)前天约好喝酒,可是,“我”当晚放了佐知子鸽子。在第18场戏,这一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转折对于影片而言,比较关键。因此,导演拿来现身说法。事实上,这个在序列中是“第18场戏”的场景处理,是一场改变原先这种无厘头、无关紧要关系的戏。导演认定这场戏的重要性,即便不给出答案,也要让观众看下去……如果处理得好,则这部三人关系的恋爱剧就有味道了。如果处理得不好,则会让电影索然无味。
这一场戏发生在东京一家快餐店,而如何在这样的场所进行空间位置,以及演员身体的场面调度,是导演的关键。演员身体(坐姿)之间呈现什么样的角度,也是关系重大的。这些因素很多。,譬如:桌子,也是主要的考量。姿势,是否面对面?更大一点的桌子,斜对角坐,也可以选择。或者用圆桌,也可以,主人公面对面坐,形成90度角。这样也未免不可。但是,最后,经过现场的商榷,导演采用了一个特殊、(饶有情趣)的现场调度。
三宅讲述了导演的经过——
前一天的彩排发现问题。我们花了足足两个小时进行弥补。各种尝试都用。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一起决定的表演。给大家讲讲过程:一开始男的独自坐在那儿。女演员可以选择坐到对面去的。如果坐在对面去了,就像要对决一样。所以就尝试了一下这种做法。男孩看不到女孩的表情和脸。女孩子坐下来,从女方的角度,表明了一种态度。后来,安排男演员坐在女演员旁边。为什么?女演员从侧面看男主。非常重要。这一幕,如果两个人面对面,表达情绪,只剩下眼神的运动。虽然这样也可以,诞生太晦涩,不清楚。因为两人在吃饭——时候的对话。这个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事实上,面对面的动作就增加了暧昧 一一不清楚。一旦两人并肩而坐。我需要观察你,就需要转头。动作显影。女孩子转头的动作非常由魅力。如果面对面。要表现女孩子对男孩子的兴趣,就需要更加夸张的动作。一旦两人的位置——并肩。要表现出魅力。就更加自然 顺畅。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刻板印象——导演是权威的。导演告诉大家怎么演。但是我自己的性格——共同创作——说不上幸福。和演员一边商量着进行(非指令的方式),通过这样的交流过程。产出的东西更加由意思。不像预期顺利——这种时候也比较多。我会想:是否场地由问题……然后调整。这样做,也许事情就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回到“第18场戏”。为什么第一天放鸽子,第二天发生肉体关系?静雄——“我”同室友,后来三人形成了一种暧昧的三人关系。佐知子后来坦白与静雄处关系。男主的面部表情非常有意思。他在夏日函馆的街头,奔跑向走远的佐知子的那场戏,也十分具有身体和表情的意义。观众自然从表情的丰富性上,读到了各种可能性。
三宅通过这样的演示,意在说明,通过表情和自然的身体动作(而不是言语和对话)来表意,这种处理方法是亚洲式的,也是日本式的,更是三宅式的。

案例3:《黎明的一切》——现场场面调度的灵感来自于互动和集体商议
在三宅的近作《黎明的一切》中,有一个关键场景。那一句台词是费脑子的?
两位主角,一位是山添,是恐慌症患者,而另一位藤泽,则也患有经前恐惧症。他们又是同事关系。互相之间的帮助,他们怎么样处理这层关系?三宅是这样考虑的:“事实上,女演员之前,这句台词怎么讲?到底怎么做才正确?现场,我和演员们费了好大劲,才最后统一意见。甭管演员个性怎么样,我都按照我事先设想好的来导演,那就没有意思。我没有采取如此保守的做法。而是在现场商量。”
在讲座现场,三宅现身说法,讲解了对演员和道具进行现场调度的两个镜头。镜头一:上台阶有鼓起勇气的味道。鼓起勇气说一番话。上台阶是一个媒介。如果在平地上,站着说话。不得不在内心酝酿情绪。地理——通过身体,带动了情绪,自然第把这个话讲出来了。镜头二:演员身体上的要素之外——门。门——半开的状态,是男人的投射。房间的样子,他不愿意外人看到。如果把门关掉,在心态上就有拒绝交流的意味。特别明显。这些东西在实际拍摄之前,没有想到的东西。之所以意识到这里成问题(因为现场被问到了)。我当时就回答说,那就开着吧,男演员还有一个动作——灵机一动,放钥匙。商量——有时候有好的结果,有时候反而进入僵局。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三宅通过这样的方式,旨在强调,在电影的拍摄实践中,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去做:先画好蓝图,然而刻板地按照这个不太科学的蓝图和草稿去做。要尝试在现场进行导演和演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发挥自己感悟力的)商量,一句话,要学会选择那些最接地气的、最适合现场和故事语境需要的场面调度。

1.应雄:《德勒兹,或喜悦的电影学》,三晋出版2025年版。
2.黄也.“观看”即“创作”:当代日本电影创作主体性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02):99-108.
3.黄也.三宅唱:表层影像的救赎可能性[J].当代电影,2020,(06):113-118.
素材来源于:https://mp.weixin.qq.com/s/b_3AhXGA2cgNwqUsDVhdfA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