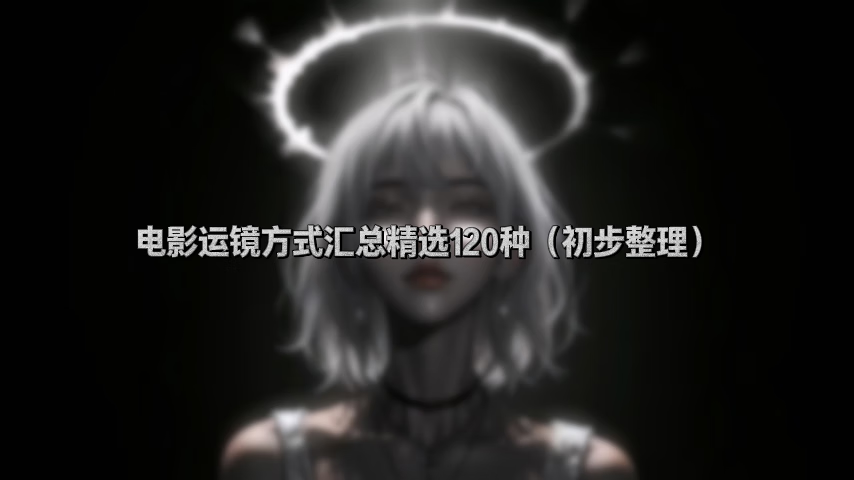自电影诞生伊始,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便萦绕在创作者与理论家的心中:电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源于对现实时空不间断的凝视与复刻,还是在于对时空碎片的解构与重组?
这一问题的两极,指向了电影叙事中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两种造型手段:长镜头+(Long Take)与蒙太奇+(Montage)。
它们不仅是技术手法的选择,更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哲学,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艺术辩论由此展开。
蒙太奇,这一源自法语“组装”之意的词汇,主张通过镜头的快速剪辑与并置,打破时空的连续性,在碎片化的影像“碰撞”中创造出全新的、超越单个镜头所能承载的意义与情感。
它是一种建构性的语言,导演如同炼金术士,在剪辑台上将现实的元素熔炼、重组,生成思想的火花。而长镜头,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以一个不间断的、持续的镜头记录下时空的流动,力求维持事件的完整性与真实感。它是一种“凝视”的艺术,导演退居幕后,让摄影机成为一扇透明的窗,邀请观众沉浸于一个看似未经雕琢的现实世界中。
这场关于电影语言的世纪之争,其理论基石由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奠定。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是蒙太奇理论的旗手,他认为电影的精髓在于“剪辑”,在于镜头间的冲突与辩证关系

而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影评家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I则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他批判蒙太奇对现实的”操纵”,并极力推崇长镜头对时空完整性的尊重,认为这才是电影最独特的使命。他们的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各自时代的电影创作,更构建了理解这两种手法的基本框架。

在深入探讨历史与理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清晰地界定蒙太奇与长镜头的概念。这不仅是对技术术语的辨析,更是对两种创作世界观的理解。它们分别代表了导演与现实、与观众沟通的两种根本性路径:一种是主动建构,另一种是邀请观察。
蒙太奇(Montage)一词源于法语”assemblage”,意为”组装”或”剪辑”。在电影中,它特指一种将一系列独立的、通常是短暂的镜头编辑、并置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连续序列的技巧。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组合,达到压缩时空、高效传递大量信息、并创造出单个镜头本身所不具备的全新意义或强烈情感冲击的效果。
蒙太奇的本质是一种省略式和建构性的叙事。它相信,电影的意义并非存在于单个镜头之内,而是诞生于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接缝”处。正如苏联蒙太奇理论家所主张的,这是一种“1+>2″的辩证过程,两个镜头的并置能产生一个全新的概念或思想。
主要功能:
叙事功能:这是蒙太奇最常见的用途,尤其是在好菜坞电影中。它可以快速展现时间的流逝,例如《洛奇》系列中主角艰苦的训练过程;或者在短时间内交代复杂的背景信息、并置多条故事线索,如《教父》中著名的”洗礼”蒙太奇,将迈克柯里昂成为教父的宗教仪式与他对家族敌人的血腥清洗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讽。
表意功能:这是苏联蒙太奇学派+的核心追求。通过将看似不相关的镜头并列,创造出隐喻和抽象思想。例如,将罢工工人被屠杀的画面与宰牛的画面剪辑在一起,以此来强化压迫的残暴性。这种手法旨在引导观众进行理智思考,而不仅仅是情感投入。
蒙太奇段落通常具有鲜明的特征,包括快速的剪辑节奏、省略式的叙事逻辑、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并且常常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或解释性的画外音,以统一整个序列的情感基调和信息流。
长镜头(Long Take),也被称为”连续镜头”(Continuous Shot)或”oner”,指的是一个持续时间远超电影常规剪辑节奏的、不间断的单一镜头。它可能持续数分钟,期间摄影机可能会进行复杂的运动,如推、拉、摇、移,并配合演员精密的场面调度。
与蒙太奇的“建构”哲学相反,长镜头的核心在于“呈现”。它试图保持时空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给予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仿佛他们正以自己的眼睛实时观察着事件的发生。这种手法将叙事的重心从剪辑台转移到了摄影机前的世界,即”场面调度”(Mise-en-scène)一包括布景、灯光、演员走位和表演等所有在镜头前发生的元素。
主要功能:
增强现实感:通过模拟人眼对现实世界的连续观察,长镜头创造了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和在场感。它避免了剪辑对时空的切割,让观众能够完整地体验一个事件的自然流程,从而增强影片的可信度。
构建场面调度:在长镜头中,信息的传递和戏剧冲突的展开依赖于镜头内部的元素变化。导演通过精心的演员走位、摄影机运动和景深变化,来引导观众的注意力,展现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动态变化。
营造紧张感与情绪:通过延缓剪辑的介入,长镜头能够让紧张感和情绪在不间断的时间流逝中持续累积。观众被迫与角色一同“等待”,体验那种悬而未决的焦虑。阿方索卡隆在《人类之子》中运用的多个长镜头,便成功地将观众置于极度不安和混乱的氛围中。
此外,必须明确区分”长镜头”(Long Take))与”远景镜头””(Long Shot)。前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指镜头持续的时长;后者则是一个空间维度的概念,指摄影机与被摄主体之间的距离。一个长镜头完全可以是近景或特写,反之一个远景镜头也可能非常短暂。
蒙太奇与长镜头的关系,最初并非和谐共存,而是在理论层面表现为一场尖锐的、几乎水火不容的对峙。这场论战的核心人物,正是苏联的爱森斯坦与法国的巴赞。他们的思想不仅定义了两种手法的理论内涵,更深刻地塑造了20世纪电影理论的基本版图,其影响延续至今。
苏联蒙太奇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它深深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革命后的社会土壤。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下,电影被视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工具。列宁本人就曾指出:“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列夫·库里肖夫、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吉加维尔托夫以及集大成者谢尔盖·爱森斯坦为代表的电影人,开始探索一种能够最有效地传达革命思想、激发观众情感的电影语言。
在众多理论家中,爱森斯坦的“冲突蒙太奇”(或称“辩证蒙太奇”)理论最具革命性和影响力。他深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日本象形文字的启发,认为电影艺术的真正力量并非来自镜头的平滑连接,而是源于两个独立镜头之间的”碰撞”(collision)。他主张,正如正题与反题的冲突产生合题,两
个并置的镜头(A和B)会产生一个全新的概念(C),这个概念C并不包含在A或B任何一个镜头之内。例如,一个镜头是“眼睛”,另一个镜头是“水”,并置在一起就产生了“哭泣”的概念。对于爱森斯坦而言,剪辑不是简单的叙事工具,而是一种思想的生成器。
为了系统化自己的理论,爱森斯坦提出了五种蒙太奇的组织方法,它们层层递进,从物理性走向思想性:
1.节拍蒙太奇(Metric Montage):完全基于镜头长短的绝对节拍进行剪辑,不考虑内容。通过加快剪辑速度来制造紧张感,但可能因其机械性而显得混乱。
2.节奏蒙太奇(Rhythmic Montage):考虑镜头内部的运动和内容来决定剪辑点,追求视觉节奏的和谐或冲突。这是最常见的剪辑形式,如《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片段,士兵们整齐划一、冷酷无情的下行步伐与民众慌乱奔逃的混乱节奏形成强烈对比。
3.音调蒙太奇(Tonal Montage):基于镜头的情感基调(光线、构图、氛围)进行剪辑。追求的是情感上的共鸣或反差,例如将柔和光线下的宁静场景与阴暗压抑的场景连接。
4.泛音/复合蒙太奇(Overtonal/Associational Montage):这是前三种方法的综合体,通过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一种生理-心理上的复合感受,即“泛音”。
5.理性蒙太奇(Intellectual Montage):最高级的蒙太奇形式,旨在通过镜头的并置直接传达抽象的、理性的思想。最著名的例子来自爱森斯坦的电影《罢工》,他将屠杀罢工工人的血腥场面与屠宰场里公牛被割喉的镜头交叉剪辑。这里的目的非常明确:将工人的遭遇比作牲畜被屠宰,以此来控诉压迫者的残暴和非人道。
对于爱森斯坦和整个苏联蒙太奇学派而言,现实只是供导演取材的“原材料”。导演的职责是通过剪辑这把手术刀,对现实进行解剖、重塑和概念化,从而主动地、强有力地构建和引导观众的感知与思考。电影是对现实的改造,而非简单的复刻。
二战后,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提出了与爱森斯坦截然相反的观点。他将电影史划分为两大阵营:“信奉影像的导演”和“信奉现实的导演”。爱森斯坦无疑属于前者。巴赞认为,爱森斯坦式的“强迫性”蒙太奇通过预设的并置和快速剪辑,强行灌输给观众一个单一的、明确的意义,这剥夺了现实世界固有的“模糊性”(ambiguity)。在巴赞看来,现实本身是多义的、复杂的,而蒙太奇则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化和操纵,它“囚禁了观众”。
巴赞极力推崇长镜头和景深镜头(DeepFocus),认为这两种技术才是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真正使命所在。
他认为:
长镜头能够保持事件发生的时空完整性。它不像蒙太奇那样将时间切成碎片,而是呈现一段连续的时间流,让观众能够完整地见证一个情境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景深镜头则在一个画面内同时保持前景、中景和后景的清晰度,从而在一个镜头内部创造了空间的纵深感和层次感。这使得导演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安排多个事件同时发生,而观众的视线则可以自由地在画面的不同区域之间游走、探索和选择。
巴赞的理论深受现象学哲学的影响。他认为,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组合最能模拟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视觉经验——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是一个连续、完整、充满多义性的时空整体。因此,这种电影语言提供了一种更“真实”、更“客观”、也更“民主”的观看方式。它没有强迫观众去看什么、去想什么,而是将一个包含了丰富信息的“现实切片”呈现在观众面前,将解读和判断的权利交还给了观众。他高度赞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如《偷自行车的人》)和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认为这些作品正是其理论的完美实践。
对于巴赞而言,电影的最高使命是“揭示”(reveal)现实,而非“创造”(create)现实。导演应该尽可能地“隐身”,让剪辑变得“不可见”,使摄影机成为一扇观察世界的透明窗口。电影的魔力不应来自剪辑的技巧,而应来自对现实本身所蕴含的戏剧性和诗意的捕捉。
理论的论战为电影创作划定了两条看似泾渭分明的道路。然而,在电影史的实际发展中,蒙太奇与长镜头的关系远比理论上的二元对立要复杂得多。它们在不同的电影运动、国家和历史时期中,被以各种方式运用、改造、融合,展现出从尖锐对立走向实践共存的动态演进过程。
在电影诞生初期,长镜头并非一种美学选择,而是一种技术上的必然。早期的摄影机胶片盘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拍摄约一分钟的长度,因此一部电影就是由若干个这样的“长镜头”组成的。这些早期的作品,如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更像是对现实片段的直接记录。然而,剪辑思维的萌芽也几乎同时出现。法国魔术师导演乔治·梅里爱在他的《月球旅行记》(1902)中,通过停机再拍等手段,实现了场景的切换和魔幻效果的创造,这可以被视为最早的蒙太奇思维雏形,其目的在于叙事和创造奇观。
德国表现主义与好莱坞经典时期:
德国表现主义(1920s):在一战后德国社会普遍的创伤和焦虑情绪下,德国表现主义电影追求的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人物内心的主观世界。为了外化角色扭曲、疯狂的心理状态,导演们大量运用了充满表现力的剪辑手法。通过非理性的镜头组合、怪异的节奏和视觉上的变形,创造出一种梦魔般的氛围,这与苏联蒙太奇的理性思辨不同,更侧重于情绪的直接渲染。
好莱坞经典时期(1930s-1950s):在制片厂制度下,好莱坞发展出了一套以”无痕剪辑”(Continuity Editing)为核心的剪辑体系。其首要目标是让观众感觉不到剪辑的存在,从而流畅地、清晰地讲述一个故事,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叙事中。然而,一种特殊形式的蒙太奇一”好莱坞式蒙太奇”一却被广泛使用。这种蒙太奇通常配以音乐,用一系列快速闪过的画面来浓缩叙事,例如表现主角的成长、一段旅程的跨越、或是报纸头条展示时间的推移。其功能是纯粹的叙事效率,与苏联蒙太奇的政治和思想意图大相径庭。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1940s-1950s):作为安德烈·巴赞理论的最佳佐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在
二战后的废墟上诞生。导演们渴望摆脱法西斯时期粉饰太平的“白色电话片”,转而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为了追求对战后社会现实的客观呈现,他们大量采用长镜头、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和纪实风格的摄影。在维托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中,长镜头跟随着失业的父亲和儿子在罗马街头绝望地寻找,其不加修饰的纪实感,让观众深切地体会到人物的困境与时代的悲哀。这种对现实的尊重和对长镜头美学的自觉运用,使其成为巴赞现实主义理论的典范。
法国新浪潮(1950s末-1960s):如果说新现实主义是对一种理论的实践,那么法国新浪潮则是一场对所有传统电影语言的全面颠覆与重塑。这群从《电影手册》走出的影评人导演,深受巴赞“作者论”的影响,但他们的实践却远比巴赞的理论更加激进和多元。他们同时拥抱并改造了蒙太奇与长镜头:
让-吕克·戈达尔的跳切(JumpCut):在《精疲力尽》中,戈达尔大量使用了“跳切”,即在同一机位拍摄的连续动作中剪掉中间一小段,造成画面人物位置的突然跳动。这是一种对“无痕剪辑”规则的公然挑衅,是蒙太奇思维的极端化体现。它不断提醒观众电影的建构性,打破了叙事的幻觉,强调了导演的存在。
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人的长镜头:与此同时,特吕弗等导演则继承了巴赞的美学,偏爱使用自由、 轻便的手持摄影机拍摄长镜头。在《四百击》的结尾,摄影机长时间地跟随着主角安托万在海边奔跑,这个著名的长镜头充满了呼吸感和即兴感,完美地传达了角色奔向未知未来的复杂心境。
法国新浪潮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蒙太奇与长镜头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它们都可以成为导演表达个人世界观和情感的有力工具。选择哪一种手法,或如何将它们结合,取决于导演的“作者风格”(auteur style)和影片的具体需求。这场运动标志着两种手法从理论对峙走向了创作实践的自觉融合。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数字时代以来,蒙太奇与长镜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早期的理论束缚逐渐被消解,当代导演们不再将它们视为非此即彼的教条,而是根据个人化的美学追求和叙事需求,自由地、创造性地进行调和与融合。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从根本上模糊了二者的界限,催生出前所未有的视觉语言。
早在理论纷争最激烈的时代,一些天才导演就已经在实践中超越了二元对立,展现出惊人的融合能力。
奥逊·威尔斯与“内部蒙太奇”:年仅25岁的奥逊威尔斯在《公民凯恩》(1941)中,与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德
一起,将景深镜头的美学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在一个长镜头内部,通过精妙的构图和场面调度,使得前景、中景、后景同时发生着不同的、具有叙事意义的事件。例如,在凯恩童年时期的著名场景中,前景是他的父母和银行家在签订转让抚养权的协议,而透过窗户,我们能看到远景中童年凯恩在雪地里快乐地玩要。这一个镜头之内,就包含了童年的纯真、成人世界的冷酷交易以及命运的转折点,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和信息“碰撞”。巴赞将这种手法称为“内部蒙太奇”(Internal Montage),它在维持时空完整性(长镜头的特性)的同时,实现了信息和思想的并置(蒙太奇的效果),堪称对两种美学的完美调和。
黑泽明与“动作即戏剧”:日本电影天皇黑泽明以其对动态画面的极致掌控而闻名。在他的史诗巨作《七武士》(1954)中,他并没有简单地选择长镜头来记录混乱的战斗,也没有滥用快速剪辑来制造表面刺激。相反,他将两者巧妙结合。他常常使用多个机位同时拍摄,然后在剪辑时,通过极其精准、有力的剪辑(蒙太奇),清晰地呈现出每一个动作的因果链条和战术意图。同时,他又非常注重镜头内部的运动一一无论是人物的奔跑、马匹的驰骋,还是天气的变化(风、雨),都成为场面调度的一部分。这种将凌厉剪辑与充满内在动感的画面相结合的方式,使得他的动作场面既有极高的信息密度和清晰度,又充满了磅礴的气势和情感张力。他真正实现了“通过动作讲述戏剧”,而不是让动作脱离于戏剧。
20世纪70年代的“新好莱坞”导演们,深受欧洲艺术电影(尤其是法国新浪潮)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在商业片的框架内融入了强烈的作者风格。
马丁·斯科塞斯与音乐蒙太奇:斯科塞斯是运用蒙太奇的大师。他标志性的手法是,将一系列快速剪辑的画面与精心挑选的流行音乐和充满主观色彩的画外音结合在一起。在《好家伙》中,他用一个经典的蒙太奇段落,配着歌曲《Layla》的后半段钢琴曲,展现了抢劫案后同伙们被逐一灭口的血腥过程。这种视听结合的蒙太奇,不仅极大地压缩了叙事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心理节奏和情感氛围,让观众迅速进入角色的世界观和精神状态。他的蒙太奇既有叙事功能,又充满了作者的情感表达和风格烙印。
·昆汀·塔伦蒂诺与张力的游戏: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则在长镜头与蒙太奇的极端张力之间游走。他以其充满机锋、喋喋不休的长时间对话场景而著称。在这些场景中,他常常使用静态或缓慢移动的长镜头,让紧张感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对话中慢慢积累,观众的心弦被越绷越紧。然后,在张力达到顶点的瞬间,他会用一组极其突兀、快速、凌厉的剪辑和极度风格化的暴力场面,将积累的情绪瞬间引爆。这种从极静(长镜头)到极动(蒙太奇)的骤然转变,构成了他独特的暴力美学。此外,他热衷于非线性叙事,将故事打碎再重组,这本身就是一种在宏观结构层面上的蒙太奇实践。
进入21世纪,数字摄影、计算机生成影像(CGI)和无缝拼接技术的成熟,彻底改变了长镜头的制作方式。过去受制于胶片长度、摄影机重量和物理空间限制的“不可能的长镜头”,如今可以通过后期技术“缝合”多个短镜头来实现,从而创造出一种天衣无缝的连续运动幻觉 。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是这场革命的先锋。在他与摄影师艾曼努尔·卢贝兹基合作的《人类之子》(2006)中,多个惊心动魄的数字长镜头将观众“扔”进了混乱的战场和飞驰的汽车内。著名的车内遇袭场景,是一个长达数分钟的、摄影机在狭窄车厢内360度自由穿梭的镜头,它以前所未有的主观沉浸感,让观众切身体会到角色的恐惧和突如其来的暴力。在《地心引力》(2013)中,开场长达17分钟的长镜头则将观众带入浩瀚而危险的太空,完美地营造了失重状态下的孤独与绝望 。
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在《1917》(2019)中,将“伪长镜头”美学推向了极致。整部电影被设计成看起来像是由两个不间断的镜头构成,实时追踪两名士兵穿越敌方战线传递情报的完整任务。这种手法将长镜头的“实时感”与战争的紧迫性、任务的连续性完美地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令人窒息的观影体验。观众被迫与主角同步前进,无法喘息,也无法从任何其他视角获得信息,从而最大化了悬念和代入感 。
数字长镜头的出现,引发了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当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长镜头,其本质是由无数个短镜头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蒙太奇”拼接而成时,爱森斯坦的建构手段与巴赞的现实理想之间的界限是否已经彻底模糊?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导演们通过最极致的“操纵”和“建构”(数字蒙太奇),最终实现了巴赞所追求的、最极致的“现实幻觉”(时空完整性)。这或许意味着,在数字时代,这场世纪之争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了和解与统一。电影语言的可能性,也因此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回顾蒙太奇与长镜头在电影史中超过一个世纪的纠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尖锐对立到复杂共生的演进轨迹。这场始于剪辑台上的哲学辩论,最终在银幕上绽放出千姿百态的艺术花朵。
二者的关系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理论上的尖锐对立,以爱森斯坦的建构主义和巴赞的现实主义为代表,他们分别将蒙太奇和长镜头提升到电影本体论的高度,视对方为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其次是实践中的并行发展与初步融合,从好莱坞的功能性蒙太奇,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长镜头的自觉运用,再到法国新浪潮对两种手法的激进实验,导演们开始将它们视为“作者风格”的工具,而非必须遵守的教条。奥逊·威尔斯和黑泽明等大师更是早早地在作品中展现了融合两种美学的可能性。最后是当代创作中的高度融合与互为表里,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长镜头本身可以由蒙太奇手段构成,二者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共同服务于创造沉浸式体验和实现导演独特视野的目标。
蒙太奇与长镜头的关系,最终证明并非一场“谁优谁劣”的零和博弈。它们是电影创作者工具箱中两种最基本、也最强大的语言工具,共同指向了电影艺术的核心——如何“雕刻时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语)和组织观众的感知体验。蒙太奇通过时间的碎裂与重组来构建节奏与思想,而长镜头则通过时间的连续流逝来营造氛围与真实。它们就像音乐中的快板与慢板,诗歌中的对仗与长句,共同构成了电影语言的韵律与结构。
电影的魅力,恰恰在于这种由对立手法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之中。选择激烈的剪辑,还是选择沉静的凝视,亦或是探索两者之间无限的组合方式,最终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讲述一个好故事,传达一种真切的情感。这场始于20世纪初的哲学辩论,至今仍在以新的形式延续,并不断激发着电影创作者们去探索、去创新。在技术不断迭代的未来,蒙太奇与长镜头必将演化出更多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形态,继续书写电影语言的无限可能。
相关文章